作者: 馬琛 發布時間: 2023-10-1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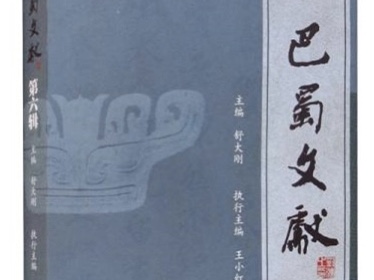
清以後,我國學術研究重心有一個從經學到史學的轉變,即羅志田先生所謂的“經學邊緣化與史學走向中心”。① 史學研究出現井噴式發展,1902年9月,馬敘倫更在《史學總論》(《新世界學報》第一期)一文中提出史學為“一國文明之所寄”。與此同時,經學不僅伴隨著孔子走下神壇而失去神聖性,還受到多方詰難,甚至連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成為問題。李澄源《經學通論》作於1942年,在此之前三十四年之間,有周予同《經今古文學》(1926)、《群經概論》(1931)、日本學者本田成之《中國經學史》(1927)、錢穆《國學概論》(1931)、馬宗霍《中國經學史》(1936)等經學通論性著作,這些學者無不擔憂著經學前途,但在他們的著作中,經學或被視作瞭解供批判的對象,或被“國學”“六藝”這樣的名目所取代,或僅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一部分。在新學科體系的概念中,經學確實已經消亡,但治經學者不亡,經學文本不亡,馬宗霍《中國經學史》被《中國學術史著作提要》評為“經學消亡之後中國人自己創作的第一部有影響的經學通史著作”。傳承如斯,即有如李源澄者,繼作《經學通論》,欲使經學再明於世,這是一本民國時期最後的經學的通史、通論,也是一本被遺忘的經學著作。
一、正名:經學消亡背景下再談經的本質問題
辛亥革命後,經學科廢,西風東漸,經學地位岌岌可危。章太炎在《訄書》裡說:“孔氏,古良史也。輔以丘明而次《春秋》,料比百家,若旋璣玉鬥矣。談、遷嗣之,後有《七略》。孔子死,名實足以伉者,漢之劉歆。”② 章太炎以六經皆史官之遺,即史書,以孔子為“古良史也”,從而將孔子拉下神壇,歸到左丘明,司馬談、司馬遷父子,劉歆的史家脈絡中。然後又說經其實就是用繩子穿起來的簡牘,將經典作為“常”“法”的意義瓦解了。雖然章太炎的本意只是為了對抗今文經學,但後果卻是直接導致了經學的潰亡,使經學地位淪落到與子學一樣。
章門弟子發揮師說,繼續瓦解經學。主政北大歷史系朱希祖師承章太炎,其主張“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,無論哪一國的史學學說,都應當介紹進來”,③使瓦解後的經學接上了西方現代學術的思路。古文經學派採用訓詁學的方法來解釋“經”,如劉師培(1884-1919)根據古文學派許慎《說文》,說“蓋經字之義,取象治絲,縱絲為經,衡絲為緯,引申之,則為組織之義……古人見經文多文言也,於是假治絲之義而錫以《六經》之名……即群書之用文言者,亦稱之為經,以與鄙詞示異……後世以降,以《六經》為先王之舊典也,乃訓經為法。又以《六經》為盡人所共習也,乃訓經為常……不明經字之本訓,安知《六經》為古代文章之祖哉!”④認為“經”是用治絲來比喻語言組織,用文言文寫成的書就叫做經,全面否定“經”中蘊含微言大義。疑古學派興起後,孔子和經的神聖性被徹底打破,即使如周予同這樣的經學大家,也在《經今古文學》(1926年2月作)中認為應“從歷史入手,由瞭解經學而否定經學”。⑤ 1962年,顧頡剛仍說:“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釋過,‘經’乃是絲線的意思,竹木簡必須用了絲線編起來捆起,才可以使它不散亂。可見這原是一種平常的工具,沒有什麼崇高的意義可言。”⑥
在這樣一種經學地位極速下降的氛圍下,以廖平、蒙文通、李源澄等為代表的蜀中學人卻始終對經學持堅守態度。光緒元年(1875),張之洞在蜀中創辦尊經書院,廖平(1852-1932)作為尊經書院早期學員,以《今古學考》奠定學術地位,引領蜀學復興。《今古學考》以禮制分今古學,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經學體系,其後廖平學術經歷“六變”,王汎森總結說:“廖平認為自己是一位哲學家,他的哲學體系建立在經學研究上,為了追趕時勢,他不斷地變造這個體系,所以出現了所謂的‘六變’,只要我們稍稍留意便會發現這‘六變’大抵對應西方文化不同階段的挑戰,廖平每次調整他的體系幾乎都是在回應他所認識到的危機,並以改造古代學術體系來維持孔子之學的相對優越性———不只優於中國各家各派,也優於全世界。”⑦廖平始終尊孔尊經,不斷調整經學體系以維持經學發展,使得蜀學始終以維護經學為核心。蒙文通(1894-1968)作為廖平高足,其學問雖由經入史,但在維護經學核心地位上態度堅決,他說:“由秦漢至明清,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,思想與行為、政治與風習,皆不能出其軌範。雖二千年學術屢有變化,派別因之亦多,然皆不過闡發之方面不同,而中心則莫之能異。其力量之宏偉,影響之深廣,遠非子、史、文藝可與抗衡。”⑧
李源澄於1928年考入“四川國學專門學校”,時蒙文通為該校教員,兼教務長,以《經學抉原》為教材教習經學,李源澄深得師傳,後又經蒙文通引薦,於1929年前往井研廖平住處,得廖平答疑解惑,成為廖平關門弟子。1932年後,李源澄又去南京、蘇州,從歐陽漸、章太炎學,李源澄耳濡目染章太炎學說,仍然信從廖平一脈的今文經學。李源澄遊學後回蜀作《經學通論》,其中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是:“經學之經,以常法為正解,不必求經字之本義。然經學雖漢人始有之,而經之得名,則在於戰國之世。故常法為經學之本義,而非經之達詁。近世釋經義者,皆釋經字之義,而非經學之經之義也。”“經”字本義與“經學”之“經”是兩回事,要解釋“經學”之經,不必求諸“經”字之本義。“經學”就是不變之常法。
在為經學正名後,李源澄旋即論證經學的地位。從當時的學術氛圍來看,中國傳統四部中的史、子、集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去處,而位於四部之首的經學卻漫無根柢,流落到史、子中,導致人們不知道如何定位經。李源澄說,四部內容可以簡單劃分成“理”與“事”,“于事則史,於理則子”,經雖非史非子,但卻包含事與理,經學是事與理的合流,也是史與子的合流,但它高於史與子,因為它所推之理,是理的最高標準。《白虎通》說:“《樂》仁、《書》義、《禮》禮、《易》知、《詩》信”,仁義禮智信正是經學賦予的不變常法,這是漢代人及漢人以前人推崇經學的意義所在。此後,經學一直以這種不變常法陶鑄人心,塑造中國人的良好品質,因此李源澄說“經學為陶鑄吾國二千年歷史之學問,吾國文化史之中心”,是一種高於史、子、集的存在。
放眼全國,在經歷“打到孔家店”運動後,孔子、經書幾乎為全國學者唾棄,李源澄寫於1942年的《經學通論》,可謂驚濤駭浪中一座寧靜的孤島,《經學通論》所澤育的蜀中學人,也成為傳統經學的一方守衛者。
二、重建:李源澄在經學自我重建問題上的思考
清末民初,史學、經學其實都經歷了一個自我批判的過程。傳統史學所遭受的詰難並不少於經學,1902年,梁啟超發表《新史學》,對傳統史學進行猛烈批判,歸納傳統史學有“四弊二病”,並由此產生“三惡果”。⑨ 然而,在徹底批判傳統史學後,梁啟超即對史學做了重新界定,並指出建設新史學之路徑及現實意義。相比經學,史學迅速找到其存在的位置,很好地完成了現代化轉變,如輿地學轉化成歷史地理學,研究蒙元史維護本國拓展疆域之偉建……無論在自我批判、研究領域、研究方法,還是研究價值上,史學都重新找到了定位。然而,經學卻始終停留在自我批判上,越演越過,呈現消亡之勢。
今天引起我們深刻思考的問題,或許正是當年李源澄苦苦思索的。李澄源《經學通論》曾多次提到目錄學家不立經學之名。1925年12月,陸懋德在《清華學報》第2卷第2期發表《中國經書之分析》,認為經書都是周代人纂述之書,將諸經分為三類,《易經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《孟子》《禮記》列入哲學類,《書經》《春秋三傳》《周禮》《儀禮》列入史學類,《詩經》《爾雅》列入文學類。經學已被明確肢解為哲學、史學、文學三類。姚名達(1905-1942)的《中國目錄學史》(1938),其僅在專科目錄篇列了一個“經解目錄”,只是共二三十目中的其中一目。在現代學科體系下,確實很難有經學一目的立足之地。正是基於對經學前途的深刻擔憂,以及實際教學需要,李源澄在回到四川,繼續從事教育事業後,寫下這本為經學正名並思考出路的著作,這本著作,也成為民國最後一本經學史著作。
經學走到這一時期,辨學術史是非、申說經義等已不是首要問題,維護其存在合理性、尋找經學存在的意義才是學者思考的重點。為何傳統史學能夠在自我批判後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很好地完成了現代化轉化,成為新史學,經學就不可以?經學之所以在受到批判後迷失方向,有兩個主要原因。
一是經學為中國所獨有,從來沒有一套可供借鑒的外來理論。史學理論在西方各國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,梁啟超、馬敘倫等鼓吹史學者,都是從西方史學理論中尋找方法,為中國史學確立新的標準和範式。經學若想獲得與史學一樣的地位,必須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。1902年7月11日,鄧實(1877-1951)在《政藝通報》第2期刊載《論經學有關於國政》,說明經學對政治的重要性。同年9月2日,陳黻宸在《新世界學報》第1期發表《經術大同說》,論述經學在新時代的轉化復興路徑。可見,在史學、經學受批判的同時期,仍有不少學者在挽留經學地位,並為經學尋找出路,然而,在李源澄成長的階段,經學始終沒能找到出路,反而走向消亡。究其原因,最主要的就在於經學沒有一套外來的標準範式。當時學者已經習慣向西方學習,借鑒外來理論,凡中國的學術都被打上外來烙印,向外尋找理論的學者根本無法為經學找到出路,就走上了絕路。
二是經學本身存在今古文之爭,內部分化致使論爭不休。今古文問題是從漢代以來一直延續的學術問題,今、古兩派此消彼長,在經學文本、治學方法、學術追求上都存在巨大差異。民國時期古文派恪守傳統,被當時認為老古董;今文派又在經典詮釋上過於求新,以向西學靠近,失去經典本意。兩派在諸多問題上互相攻擊,導致經學越辨越亂,最後成為說不清的東西,而被肢解。
在上述兩個問題上,李源澄都是反其道而行之,成為當時學術主流中一支細微的逆流。
其一,反向外之主流而向內。在學術主流西化的背景下,李源澄向內回歸,從中國的歷史中尋找經學。《經學通論》完全是一部傳統的學術專著,從經學歷史到專經介紹,均是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《經學通論》之類的傳統路數。但比起之前的著作,多了一些對經學地位的強調。從歷史來看,經學是“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”,經學如“日月經天”,“評論政治得失,衡量人物優劣,皆以經學為權衡”。在李源澄看來,經學不必向外尋找與哲學、社會科學、法學等西方學科的關聯,這些新興學科僅僅新在名詞,在本國固有的歷史中,均能找到它們的身影,而經學則是這一切的統帥。經學在漢代強調外王之學,在宋代強調內聖之學,而在當代,正需要重新認識經學內聖外王的功效,將它重新塑造成關係本國政治發展的學問。
其二,反分古今之主流而主和。李源澄對今古文的認識十分深刻,觀察李源澄的學習歷程,可略知一二,李源澄先從今文學派蒙文通、廖平學,時“四川國學專門學校”中還有龔道耕、吳之英、劉師培這樣的經學大家,各派相與切磋,李源澄擇善而從。1935年9月,章太炎在蘇州創辦“章氏國學講習會”。李源澄應章太炎之邀,入講習會,從章太炎學,時章太炎68歲,李源澄27歲。李源澄守廖平今文經學,古文經學派章太炎不僅“不以為忤”,反而給予先生極高的評價。李源澄兼聞今古文學之精髓,又形成了自己的今古學觀。本書在通經論述時,皆採用廖平、龔道耕、蒙文通之說,讀此書者,能對經學諸多基本問題有所把握。在具體介紹經文時,本書又採用古文經學排序方式,且經文具體解說上多採用章太炎之說。其在《經學通論》中總結說:“通經致用,今學為優;釋文正讀,古學為最。”這是李源澄在向今古兩派大家學習後得出的深刻認識。古文經學側重治學,今文經學側重致用,在李源澄心中,今文經學的地位要高於古文經學。他還明確提出以“經”與“經說”分別為說之論。今古文蓋經之文本,起先只是今古文本的不同。今古學則經之解說,今古學不同發生在今古文不同之後。今學“通經致用”,這是基本價值觀問題,古學“釋文正讀”,這是治學路徑問題,也即廖平先生所說的“今學為哲學,古學為史學”。
學者的可貴之處在于能夠發先聲、發不同聲。李源澄《經學通論》的可貴之處正在于發不同聲。李源澄師蒙文通曾言:“觀水有術,必觀其瀾。”即研究歷史應該抓住大事件研究,然而李源澄更多了一層思考,即研究那一時期的學術思想,以發現經學對大事件發生的影響。故而李源澄治學經歷了由經到子,由子到史,又回到以史證經的路上。對經學根基的留戀,使得其在史學道路上數次深情的回望,最終堅持了以史證經的路數。在總體思想上,李源澄可謂一位偉大的時代逆行者。
在經學教學的具體問題上,李源澄也做出了一些思考。大抵受中國傳統教育者,均知經學之重要性,如國粹派,鄧實《論經學有關於國政》,認為“六經者,人才之根本也,人才者,國家之命脈也,是故以經學成人才,以人才維國運,古今興亡,罔不由此。”但在如何維持經學教育的問題上,只能空喊口號,無所建樹。奇怪的是,當世無人質疑讀史之必要性,讀不讀經卻成了問題。以至於“讀經”發展成一場運動,需要諸學者出來倡議。⑩
李源澄提出:學習經學,“則有三事:一曰治經,二曰治經說,三曰考經學對中國文化各部分之關係。”第一,治經是治經之本文,有釋文、釋義兩條途徑。“治經者以文字始,以義理終”,這也是一條從宋代魏了翁以來確立的蜀學治學路徑,清末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,為指引學生讀書門徑而編撰成《書目答問》,書中說道:“由小學入經學者,其經學可信;由經學入史學者,其史學可信;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,其理學可信;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,其詞章有用;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,其經濟成就遠大。” ⑪這也是一條傳統學者最為認可的治學路徑。第二,治經說則“治理先儒說經之書也,先儒說經之書雖為經而作,其學術思想亦見焉”,“於其說經之文予以疏通證明,於其學術思想亦予以發揮介紹,並與他家較量以明其學術史上之地位”。李源澄十分強調發揮學術思想,這也是治學經世致用的應有之義。第三,強調研究經學對中國文化各部分的關係則是李源澄先生的新論。當世諸多學者,如錢穆等人均肯定研究史學對建設本國政治,重塑國人思想的意義,而李源澄指出,經學才是影響歷史的主因。經學影響國家建國的方針,影響國家法律實施,影響國民思維方式。與本國政治建設、思想法律、人生規律等密切相關。無論從哪種意義說,經學都十分重要,李源澄倡議說:“經學對吾國政治、社會、人心、風俗關係之大,人皆知之,而無人能剖析具陳者,此非經學歷史者一大事乎?”沿著這一思路,治經學者應當從各方面發掘經學的現實意義。
三、結語
李源澄《經學通論》幾乎為歷史埋沒,李源澄本人也被稱作“消失的學者”,近年來伴隨《李源澄全集》面世,相信這位融通今古的蜀學大家能夠重新走回大家的學術視野。本人不揣譾陋,就先生《經學通論》一書妄提拙見,以期以李源澄先生為例,還願傳統學者維護經學的努力,也為今日儒學學科重建提供一點啟示。
(原載:《巴蜀文獻》第六輯,四川大學出版社2021出版。)
注釋:
①羅志田:《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》,載《漢學研究》第15卷2期,1997年12月。
②章炳麟:《訄書》,朱維錚編校本,中西書局2012年版,第116頁。
③朱希祖:《新史學•序》,載何炳松著《新史學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,第7頁。
④劉師培:《經學教科書》,嶽麓書社2013年版,第5-6頁。
⑤周予同:《群經通論》,朱維錚編校本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86頁。
⑥顧頡剛:《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》,載《顧頡剛古史論文集》卷七,中華書局2011年版,第454頁。
⑦王汎森:《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———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》,《歷史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⑧蒙文通:《經學抉原》,載《蒙文通文集》卷三,巴蜀書社1995年版,第149頁。
⑨中國傳統史學的“四弊二病”:1、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;2、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;3、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;4、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;5、能鋪敘而不能別裁;6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。三惡果:一曰難讀,難別擇,無感觸。
⑩如嚴複《讀經當積極提倡》,章太炎《論讀經有利而無弊》,熊十力《經為常道不可不讀》等。
⑪(清)張之洞:《書目答問》附二《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》,上海:中西書局2012年版,第224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