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 喬清舉 發布時間: 2022-10-1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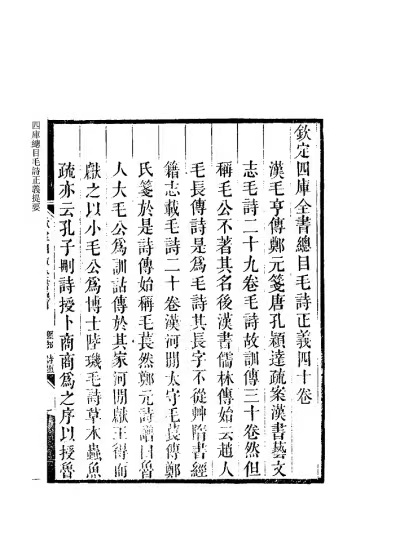
一
我們把“五四”以來形成、目前仍十分流行的《詩經》研究范式稱為現代詩經學或現代詩學。它的特點是把《詩經》只做詩講,對於其中篇章和其他的愛情、婚姻、家庭、勞作、軍事題材的詩有什麼區別,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,普遍說明不夠不透甚或闕如。《詩經》既然叫“經”,則我們對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,亦屬順理成章,可現代詩學並不能滿足我們這個願望。事實上,《詩》在歷史上是以“經”的形式而非以“詩”的形式發揮作用的,《詩》首先是“經”其次才是詩。今天應當給它一個“經”的定位,這其實也是恢復它原有的地位。
二
作為“經”和作為詩區別甚大。“經”是維繫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發展脈絡的基本文獻。《詩經》作為經在歷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、培養人的溫柔敦厚的中正性情,這叫“詩教”。孔子說“詩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無邪”,可謂是對《詩》作為經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練的說明。《禮記》記載:“入其國,其教可知也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,《詩》教也。”《詩經》通過比喻、聯想等文學手段感發人的心志情意,使人從美的情感體驗上升到善的理性認知,在性情、人格與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。把《詩》作為經就是把它作為塑造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傳統、文明傳統的典籍對待。
《詩經》是中華文化重德傳統的一個重要源頭。《論語》講“為政以德”。《大學》三綱領第一條就是“明明德”,首個“明”是動詞,義為彰顯;次“明”是形容詞,義為光明。在儒家文化中,道德具有照耀和溫暖天下的作用。那麼,“明德”“明明德”的概念來自何處?《大雅•皇矣》有“帝遷明德”“予懷明德”,當是“明德”的來源(“明德惟馨”出於古文《尚書》,此處不用)。此篇又有“其德克明”一句,《尚書•堯典》也有“克明俊德”一句,這兩個“明”都是動詞。“明明德”當為“克明”與“明德”的結合。從歷史線索來看,從上古先秦到漢唐宋明,“明明德”的思想一以貫之。從《詩經》《尚書》到《論語》《大學》,再到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、元代科舉以《集注》為准,“明明德”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;“明明德”就屬於根與魂的範疇,是中華文化、中華文明的命脈所系。《詩經》是中華民族重德傳統的源頭。不僅如此,詩教還一直擴展至朝鮮半島、越南、日本,成為東亞共同的精神財富。
“子曰詩云”也具有重要的經學意義。“子曰詩云”不僅是一種表達方式,其實也是一種文體、一種思維方式、一種教化方式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中常見這種行文方式。通常是先說“子曰”,接著說“《詩》云”;“子曰”是觀點,“詩云”是用《詩》作為論據。從詮釋學的觀點來看,引用、解釋和使用本質上是統一的。孔曾思孟對《詩經》的運用表達了他們對《詩》的理解,他們的理解開拓了《詩》涵養性情、教化民風的意義邊界,由此構成的意義世界便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。
從“經”的角度看,通常被視為修辭手法的賦、比、興,其實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。《行葦》開頭“敦彼行葦,牛羊勿踐履。方苞方體,維葉泥泥”四句,若只作修辭上的興看,便索然無味;若作“經”看,則韻味濃郁。興類似電影中由遠漸近、漸近,然後出現人的鏡頭的表現方式。通過自然場景引出人,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,與自然具有關聯的內涵。《毛詩》即認為,此段表達了“周家忠厚,仁及草木”的道德。鄭玄提出:“仁,愛人以及物。”賈公彥解釋道:“云‘仁,愛人以及物’者,仁者內善於心,外及於物,謂若《行葦》詩美成王云‘敦彼行葦,牛羊勿踐履’,是愛人及于葦,葦即物也。”孔穎達說:“作《行葦》詩者,言忠誠而篤厚也。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,其仁恩及於草木。以草木之微,尚加愛惜,況在於人,愛之必甚。”古人把《詩》作為經,引申出“仁,愛人以及物”的哲學命題,把仁者“愛人”推進到了愛自然,這在中國思想史、文化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。可是,這些豐富內涵在現代詩學中是看不到的。
三
現代詩學問題出在何處?出在“文學”概念和世界觀上。“文學”這個詞很有意思,中文中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《論語》。孔門弟子分為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四科,子夏列在文學科。子夏是以傳經著稱的,所以這裡的“文學”其實就是文獻、文化,再具體說是經學之義。在歐洲文化中,文學(literature)也有文化的含義,如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有“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”的說法,其中“文學”的含義也是廣義的文化。現代學科分化以後,“文學”概念得到重新整合,演化為文學專業意義的文學。這種新“文學”概念只剩下《論語》“文學”概念的一部分內涵,“五四”以來的詩學從現代“文學”概念出發,把《詩經》當作文學作品,並定義為“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”,自然反映不出《詩經》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釋史。比如上引《行葦》一段,就因為只把它作為沒有實質意義的修辭,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結的文化底蘊和哲學思維,也就了無餘韻了。
“五四”以反封建著稱,但由於時代局限,也存在對於封建倫理和傳統道德中的永恆內容缺乏辨別的弊端。現代詩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剔除《詩經》解釋中的封建倫理,認為《詩經》自從成為儒家經典,被打上“思無邪”“溫柔敦厚”的標記後,成為“經夫婦,成孝敬,厚人倫,美教化,移風俗”的金科玉律,這些都不是《詩經》的本來面目。這種認識不可不謂犀利,但也難說就不偏激。“思無邪”乃孔子所說,“溫柔敦厚”系《禮記》記載,“經夫婦”一段則出自毛詩序,上述說法意味著《詩經》從孔子開始就講錯了,歷史上《詩經》解釋全無價值。照這麼下來,中華文化還有什麼可講的?況且,把《詩經》僅視作文學作品,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視為愛情詩也不符合歷史。古代帝王都是要學《詩經》的。不給他們講“樂而不淫,哀而不傷”“思無邪”“發乎情,止乎禮”的中正情感,而是講愛情,那不是把他往亡國的道路上引?直到北宋,程頤還強調“《關雎》《麟趾》之意”,強調的是夫婦家庭之道。不懂這些就很難理解《詩》,當然也難以深入地理解理學。《詩經》是塑造中華民族精神世界與文化傳統、文明傳統的第一部詩歌形式的經典,現代詩學之所以體現不出“經”的韻味,問題就出在它只把《詩經》作文學看,抽空了其積澱的精神底蘊和負載的文化價值。
這麼說,是否意味著現代《詩經》學全無價值,應該放棄呢?倒也不必。客觀、公允地說,一代有一代的《詩經》學,每一代《詩經》學都有其價值與地位。現代《詩經》學截斷眾流,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無任何文化價值觀負載的清爽的《詩經》面目,是它的特點和成就;但其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《詩經》解釋,則不免僭越。古人不可輕易否定。同樣,我們也不輕易否定現代詩學。
在《詩》產生及流傳過程中,有兩種真實,一是“源的真實”,一是“流的真實”。前者指詩篇產生的背景、主題原本是什麼,後者指《詩經》在歷史上的實際影響是什麼。研究《詩經》,不能以“源”的真實否定“流”的真實,反之亦然。比如,現代《詩經》學認為《關雎》的主題反映的是青年貴族的愛情,倘果真如此,那就是源的真實。但是,經學史上古人從未把它作為愛情詩。從孔子開始即如此,新出土的《孔子詩論》強化了這一點。《毛詩》認為是頌“後妃之德”,今文經學認為是“刺康王晏起”。看來古人的認識也不盡同,一篇兼備美刺兩說。可是,無論美、刺,皆非愛情。這則是流的真實。從流的真實看,作為經的《詩》在歷史上的作用是教化,是詩教。以教化為導向的《詩經》詮釋史既是詩義不斷被“發現”的過程,實質上又是詩義不斷被“建構”的歷史;既是《詩》作為“經”發揮作用的歷史,實質上又是其上升為“經”的歷史。《詩經》實在地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態,所以,《詩經》詮釋史與其說是解釋詩的本來意義的歷史,倒不如說是塑造詩教傳統、建構中華文化文明的歷史。
四
現代分科學術推進了研究的深入,但也造成了“道術為天下裂”的學科分隔。研究哲學不從文學中找材料,往往遺漏了“仁,愛人以及物”一類的重要史料;研究文學不做哲學提升,淡化了詩的韻味;總之都沒有把傳統文化的優秀處展示出來。看來,今後研究《詩經》,不樹立國學、中華文化學、中華文明學的學科概念,不採用辯證地統一古今詩學、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經學方式,而欲覓得《詩》作為“經”的豐富而又深刻的底蘊,未必不是緣木求魚。
(作者系中央黨校哲學部副主任、教授;來源:《光明日報》(2022年09月24日 11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