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 马琛 发布时间: 2023-10-1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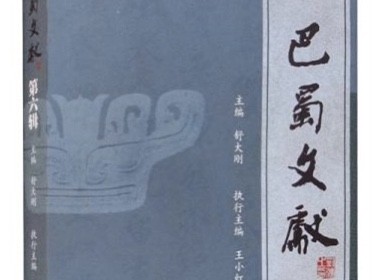
清以后,我国学术研究重心有一个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,即罗志田先生所谓的“经学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”。① 史学研究出现井喷式发展,1902年9月,马叙伦更在《史学总论》(《新世界学报》第一期)一文中提出史学为“一国文明之所寄”。与此同时,经学不仅伴随着孔子走下神坛而失去神圣性,还受到多方诘难,甚至连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成为问题。李澄源《经学通论》作于1942年,在此之前三十四年之间,有周予同《经今古文学》(1926)、《群经概论》(1931)、日本学者本田成之《中国经学史》(1927)、钱穆《国学概论》(1931)、马宗霍《中国经学史》(1936)等经学通论性著作,这些学者无不担忧着经学前途,但在他们的著作中,经学或被视作了解供批判的对象,或被“国学”“六艺”这样的名目所取代,或仅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部分。在新学科体系的概念中,经学确实已经消亡,但治经学者不亡,经学文本不亡,马宗霍《中国经学史》被《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》评为“经学消亡之后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有影响的经学通史著作”。传承如斯,即有如李源澄者,继作《经学通论》,欲使经学再明于世,这是一本民国时期最后的经学的通史、通论,也是一本被遗忘的经学著作。
一、正名:经学消亡背景下再谈经的本质问题
辛亥革命后,经学科废,西风东渐,经学地位岌岌可危。章太炎在《訄书》里说:“孔氏,古良史也。辅以丘明而次《春秋》,料比百家,若旋璣玉斗矣。谈、迁嗣之,后有《七略》。孔子死,名实足以伉者,汉之刘歆。”② 章太炎以六经皆史官之遗,即史书,以孔子为“古良史也”,从而将孔子拉下神坛,归到左丘明,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,刘歆的史家脉络中。然后又说经其实就是用绳子穿起来的简牍,将经典作为“常”“法”的意义瓦解了。虽然章太炎的本意只是为了对抗今文经学,但后果却是直接导致了经学的溃亡,使经学地位沦落到与子学一样。
章门弟子发挥师说,继续瓦解经学。主政北大历史系朱希祖师承章太炎,其主张“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,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,都应当介绍进来”,③使瓦解后的经学接上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思路。古文经学派采用训诂学的方法来解释“经”,如刘师培(1884-1919)根据古文学派许慎《说文》,说“盖经字之义,取象治丝,纵丝为经,衡丝为纬,引申之,则为组织之义……古人见经文多文言也,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《六经》之名……即群书之用文言者,亦称之为经,以与鄙词示异……后世以降,以《六经》为先王之旧典也,乃训经为法。又以《六经》为尽人所共习也,乃训经为常……不明经字之本训,安知《六经》为古代文章之祖哉!”④认为“经”是用治丝来比喻语言组织,用文言文写成的书就叫做经,全面否定“经”中蕴含微言大义。疑古学派兴起后,孔子和经的神圣性被彻底打破,即使如周予同这样的经学大家,也在《经今古文学》(1926年2月作)中认为应“从历史入手,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”。⑤ 1962年,顾颉刚仍说:“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释过,‘经’乃是丝线的意思,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来捆起,才可以使它不散乱。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,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。”⑥
在这样一种经学地位极速下降的氛围下,以廖平、蒙文通、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却始终对经学持坚守态度。光绪元年(1875),张之洞在蜀中创办尊经书院,廖平(1852-1932)作为尊经书院早期学员,以《今古学考》奠定学术地位,引领蜀学复兴。《今古学考》以礼制分今古学,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经学体系,其后廖平学术经历“六变”,王汎森总结说:“廖平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,他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学研究上,为了追赶时势,他不断地变造这个体系,所以出现了所谓的‘六变’,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便会发现这‘六变’大抵对应西方文化不同阶段的挑战,廖平每次调整他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回应他所认识到的危机,并以改造古代学术体系来维持孔子之学的相对优越性———不只优于中国各家各派,也优于全世界。”⑦廖平始终尊孔尊经,不断调整经学体系以维持经学发展,使得蜀学始终以维护经学为核心。蒙文通(1894-1968)作为廖平高足,其学问虽由经入史,但在维护经学核心地位上态度坚决,他说:“由秦汉至明清,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,思想与行为、政治与风习,皆不能出其轨范。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,派别因之亦多,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,而中心则莫之能异。其力量之宏伟,影响之深广,远非子、史、文艺可与抗衡。”⑧
李源澄于1928年考入“四川国学专门学校”,时蒙文通为该校教员,兼教务长,以《经学抉原》为教材教习经学,李源澄深得师传,后又经蒙文通引荐,于1929年前往井研廖平住处,得廖平答疑解惑,成为廖平关门弟子。1932年后,李源澄又去南京、苏州,从欧阳渐、章太炎学,李源澄耳濡目染章太炎学说,仍然信从廖平一脉的今文经学。李源澄游学后回蜀作《经学通论》,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:“经学之经,以常法为正解,不必求经字之本义。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,而经之得名,则在于战国之世。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,而非经之达诂。近世释经义者,皆释经字之义,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。”“经”字本义与“经学”之“经”是两回事,要解释“经学”之经,不必求诸“经”字之本义。“经学”就是不变之常法。
在为经学正名后,李源澄旋即论证经学的地位。从当时的学术氛围来看,中国传统四部中的史、子、集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去处,而位于四部之首的经学却漫无根柢,流落到史、子中,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定位经。李源澄说,四部内容可以简单划分成“理”与“事”,“于事则史,于理则子”,经虽非史非子,但却包含事与理,经学是事与理的合流,也是史与子的合流,但它高于史与子,因为它所推之理,是理的最高标准。《白虎通》说:“《乐》仁、《书》义、《礼》礼、《易》知、《诗》信”,仁义礼智信正是经学赋予的不变常法,这是汉代人及汉人以前人推崇经学的意义所在。此后,经学一直以这种不变常法陶铸人心,塑造中国人的良好品质,因此李源澄说“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问,吾国文化史之中心”,是一种高于史、子、集的存在。
放眼全国,在经历“打到孔家店”运动后,孔子、经书几乎为全国学者唾弃,李源澄写于1942年的《经学通论》,可谓惊涛骇浪中一座宁静的孤岛,《经学通论》所泽育的蜀中学人,也成为传统经学的一方守卫者。
二、重建:李源澄在经学自我重建问题上的思考
清末民初,史学、经学其实都经历了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。传统史学所遭受的诘难并不少于经学,1902年,梁启超发表《新史学》,对传统史学进行猛烈批判,归纳传统史学有“四弊二病”,并由此产生“三恶果”。⑨ 然而,在彻底批判传统史学后,梁启超即对史学做了重新界定,并指出建设新史学之路径及现实意义。相比经学,史学迅速找到其存在的位置,很好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变,如舆地学转化成历史地理学,研究蒙元史维护本国拓展疆域之伟建……无论在自我批判、研究领域、研究方法,还是研究价值上,史学都重新找到了定位。然而,经学却始终停留在自我批判上,越演越过,呈现消亡之势。
今天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,或许正是当年李源澄苦苦思索的。李澄源《经学通论》曾多次提到目录学家不立经学之名。1925年12月,陆懋德在《清华学报》第2卷第2期发表《中国经书之分析》,认为经书都是周代人纂述之书,将诸经分为三类,《易经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《礼记》列入哲学类,《书经》《春秋三传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列入史学类,《诗经》《尔雅》列入文学类。经学已被明确肢解为哲学、史学、文学三类。姚名达(1905-1942)的《中国目录学史》(1938),其仅在专科目录篇列了一个“经解目录”,只是共二三十目中的其中一目。在现代学科体系下,确实很难有经学一目的立足之地。正是基于对经学前途的深刻担忧,以及实际教学需要,李源澄在回到四川,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后,写下这本为经学正名并思考出路的著作,这本著作,也成为民国最后一本经学史著作。
经学走到这一时期,辨学术史是非、申说经义等已不是首要问题,维护其存在合理性、寻找经学存在的意义才是学者思考的重点。为何传统史学能够在自我批判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很好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化,成为新史学,经学就不可以?经学之所以在受到批判后迷失方向,有两个主要原因。
一是经学为中国所独有,从来没有一套可供借鉴的外来理论。史学理论在西方各国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,梁启超、马叙伦等鼓吹史学者,都是从西方史学理论中寻找方法,为中国史学确立新的标准和范式。经学若想获得与史学一样的地位,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。1902年7月11日,邓实(1877-1951)在《政艺通报》第2期刊载《论经学有关于国政》,说明经学对政治的重要性。同年9月2日,陈黻宸在《新世界学报》第1期发表《经术大同说》,论述经学在新时代的转化复兴路径。可见,在史学、经学受批判的同时期,仍有不少学者在挽留经学地位,并为经学寻找出路,然而,在李源澄成长的阶段,经学始终没能找到出路,反而走向消亡。究其原因,最主要的就在于经学没有一套外来的标准范式。当时学者已经习惯向西方学习,借鉴外来理论,凡中国的学术都被打上外来烙印,向外寻找理论的学者根本无法为经学找到出路,就走上了绝路。
二是经学本身存在今古文之争,内部分化致使论争不休。今古文问题是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的学术问题,今、古两派此消彼长,在经学文本、治学方法、学术追求上都存在巨大差异。民国时期古文派恪守传统,被当时认为老古董;今文派又在经典诠释上过于求新,以向西学靠近,失去经典本意。两派在诸多问题上互相攻击,导致经学越辨越乱,最后成为说不清的东西,而被肢解。
在上述两个问题上,李源澄都是反其道而行之,成为当时学术主流中一支细微的逆流。
其一,反向外之主流而向内。在学术主流西化的背景下,李源澄向内回归,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经学。《经学通论》完全是一部传统的学术专著,从经学历史到专经介绍,均是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《经学通论》之类的传统路数。但比起之前的著作,多了一些对经学地位的强调。从历史来看,经学是“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”,经学如“日月经天”,“评论政治得失,衡量人物优劣,皆以经学为权衡”。在李源澄看来,经学不必向外寻找与哲学、社会科学、法学等西方学科的关联,这些新兴学科仅仅新在名词,在本国固有的历史中,均能找到它们的身影,而经学则是这一切的统帅。经学在汉代强调外王之学,在宋代强调内圣之学,而在当代,正需要重新认识经学内圣外王的功效,将它重新塑造成关系本国政治发展的学问。
其二,反分古今之主流而主和。李源澄对今古文的认识十分深刻,观察李源澄的学习历程,可略知一二,李源澄先从今文学派蒙文通、廖平学,时“四川国学专门学校”中还有龚道耕、吴之英、刘师培这样的经学大家,各派相与切磋,李源澄择善而从。1935年9月,章太炎在苏州创办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。李源澄应章太炎之邀,入讲习会,从章太炎学,时章太炎68岁,李源澄27岁。李源澄守廖平今文经学,古文经学派章太炎不仅“不以为忤”,反而给予先生极高的评价。李源澄兼闻今古文学之精髓,又形成了自己的今古学观。本书在通经论述时,皆采用廖平、龚道耕、蒙文通之说,读此书者,能对经学诸多基本问题有所把握。在具体介绍经文时,本书又采用古文经学排序方式,且经文具体解说上多采用章太炎之说。其在《经学通论》中总结说:“通经致用,今学为优;释文正读,古学为最。”这是李源澄在向今古两派大家学习后得出的深刻认识。古文经学侧重治学,今文经学侧重致用,在李源澄心中,今文经学的地位要高于古文经学。他还明确提出以“经”与“经说”分别为说之论。今古文盖经之文本,起先只是今古文本的不同。今古学则经之解说,今古学不同发生在今古文不同之后。今学“通经致用”,这是基本价值观问题,古学“释文正读”,这是治学路径问题,也即廖平先生所说的“今学为哲学,古学为史学”。
学者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发先声、发不同声。李源澄《经学通论》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发不同声。李源澄师蒙文通曾言: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。”即研究历史应该抓住大事件研究,然而李源澄更多了一层思考,即研究那一时期的学术思想,以发现经学对大事件发生的影响。故而李源澄治学经历了由经到子,由子到史,又回到以史证经的路上。对经学根基的留恋,使得其在史学道路上数次深情的回望,最终坚持了以史证经的路数。在总体思想上,李源澄可谓一位伟大的时代逆行者。
在经学教学的具体问题上,李源澄也做出了一些思考。大抵受中国传统教育者,均知经学之重要性,如国粹派,邓实《论经学有关于国政》,认为“六经者,人才之根本也,人才者,国家之命脉也,是故以经学成人才,以人才维国运,古今兴亡,罔不由此。”但在如何维持经学教育的问题上,只能空喊口号,无所建树。奇怪的是,当世无人质疑读史之必要性,读不读经却成了问题。以至于“读经”发展成一场运动,需要诸学者出来倡议。⑩
李源澄提出:学习经学,“则有三事:一曰治经,二曰治经说,三曰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。”第一,治经是治经之本文,有释文、释义两条途径。“治经者以文字始,以义理终”,这也是一条从宋代魏了翁以来确立的蜀学治学路径,清末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,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撰成《书目答问》,书中说道:“由小学入经学者,其经学可信;由经学入史学者,其史学可信;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,其理学可信;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,其词章有用;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,其经济成就远大。” ⑪这也是一条传统学者最为认可的治学路径。第二,治经说则“治理先儒说经之书也,先儒说经之书虽为经而作,其学术思想亦见焉”,“于其说经之文予以疏通证明,于其学术思想亦予以发挥介绍,并与他家较量以明其学术史上之地位”。李源澄十分强调发挥学术思想,这也是治学经世致用的应有之义。第三,强调研究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的关系则是李源澄先生的新论。当世诸多学者,如钱穆等人均肯定研究史学对建设本国政治,重塑国人思想的意义,而李源澄指出,经学才是影响历史的主因。经学影响国家建国的方针,影响国家法律实施,影响国民思维方式。与本国政治建设、思想法律、人生规律等密切相关。无论从哪种意义说,经学都十分重要,李源澄倡议说:“经学对吾国政治、社会、人心、风俗关系之大,人皆知之,而无人能剖析具陈者,此非经学历史者一大事乎?”沿着这一思路,治经学者应当从各方面发掘经学的现实意义。
三、结语
李源澄《经学通论》几乎为历史埋没,李源澄本人也被称作“消失的学者”,近年来伴随《李源澄全集》面世,相信这位融通今古的蜀学大家能够重新走回大家的学术视野。本人不揣谫陋,就先生《经学通论》一书妄提拙见,以期以李源澄先生为例,还愿传统学者维护经学的努力,也为今日儒学学科重建提供一点启示。
(原载:《巴蜀文献》第六辑,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出版。)
注释:
①罗志田:《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》,载《汉学研究》第15卷2期,1997年12月。
②章炳麟:《訄书》,朱维铮编校本,中西书局2012年版,第116页。
③朱希祖:《新史学•序》,载何炳松著《新史学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,第7页。
④刘师培:《经学教科书》,岳麓书社2013年版,第5-6页。
⑤周予同:《群经通论》,朱维铮编校本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86页。
⑥顾颉刚:《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》,载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》卷七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454页。
⑦王汎森:《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———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》,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⑧蒙文通:《经学抉原》,载《蒙文通文集》卷三,巴蜀书社1995年版,第149页。
⑨中国传统史学的“四弊二病”:1、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;2、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;3、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;4、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;5、能铺叙而不能别裁;6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。三恶果:一曰难读,难别择,无感触。
⑩如严复《读经当积极提倡》,章太炎《论读经有利而无弊》,熊十力《经为常道不可不读》等。
⑪(清)张之洞:《书目答问》附二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,上海:中西书局2012年版,第224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