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 刘光胜 发布时间: 2021-10-2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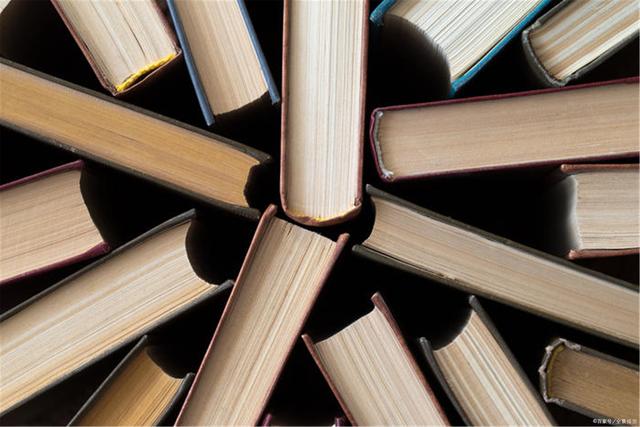
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,《尚书》上起尧、舜、禹传说时期,下讫秦穆公时代,是考察夏、商、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研究资料。然而《尚书》在流传过程中,命运多舛,屡遭劫难。2008年7月,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(以下简称“清华简”)。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、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以无字残片为标本,对清华简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,经校正后,得到清华简的时代为公元前305±30年,即战国中期偏晚。
在中国历史上,《尚书》类文献的重要发现有两次:一是伏生今文。秦始皇焚书,伏生将《尚书》藏于屋壁。西汉初年,政局稳定,伏生复求其书,得今文《尚书》29篇。二是孔壁古文。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,发现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尚书》等多部典籍,其中古文《尚书》16篇。河间献王古文《尚书》、杜林漆书等版本面世之后,随即散佚、消失,至今已无法管窥其内容。在这种意义上说,楚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竹书清华简,可谓是《书》类文献的第三次重要发现。
清华简对于《尚书》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,主要体现在:
其一,《尚书》文本的重新解读。《尚书·康诰》之“康”,马融、王肃、孔颖达等学者解释为国名,而郑玄、江声、皮锡瑞主张是谥号,两种说法相争达千年之久。清华简《系年》第四章云“(周成王、周公)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,以侯殷之余民”,说明“康叔”“康侯”“康诰”之“康”皆源于康丘。《尚书》佶屈聱牙,“于六艺中最难懂”。清华简的面世,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契机。
其二,《尚书》文体学研究。过去我们把“诰”,理解为“自上对下”的训诰,但从清华简《尹至》《尹诰》看,伊尹为臣,他可以“诰”汤。可知“诰”体有“自下而上”与“自上而下”两种方式。大盂鼎、毛公鼎等铭文中“令(命)”,包括赏赐、册命、行往、征伐等丰富的内容。清华简《祭公之顾命》名义上是“命”,却带有训诰的性质。清华简《芮良夫毖》似《书》似《诗》,体例杂糅。清华简《成人》,近似于《尚书·吕刑》之体。清华简《赤鹄之集汤之屋》虽属于《书》类文献,但文体切合“小说”的特点。以清华简《保训》《命训》为依据,可管窥“训”体之特征。这些带有原生样态的文献,使我们对《尚书》“因事而立,体例不定”的文体特征,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。
或称“六体”,或言“十例”,不过是后儒对《尚书》体例的归纳与总结。借助出土简帛文献,摆脱后世《尚书》文体观念的藩篱,重新发掘先秦《书》类文献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文体的原生态特征,则可展现其所承载的多样的文体功能。
其三,分系研究。目前《尚书》学的研究,如马士远《周秦〈尚书〉学研究》《两汉〈尚书〉学研究》、程兴丽《魏晋南北朝〈尚书〉学研究》、赵晓东《隋唐〈尚书〉学研究》、张建民《宋代〈尚书〉学研究》、古国顺《清代尚书学》、史振卿《清代〈尚书〉学若干问题研究》等,多是按照朝代顺序纵向历时性的展开。
我们认为,《尚书》学研究既要措意于纵向的演进,同时也要关注横向的延展。先秦时期,《书》类文献传流有两个重要的特征:一是多系并存。在儒家《尚书》系统之外,还有墨家、道家、清华简等不同的《书》类文献系统。二是多本别传。在不同的国家,在不同的地区,存在不同的传本。如齐鲁地区有孔子传《书》、墨子传《书》,楚地有清华简《书》类文献,郑国也有《书》。简言之,有大量的传本,游离于系统之外。
春秋战国,是《尚书》流传过程中文本变动尤为剧烈的时期。我们主张在纵向分期的基础之上,将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及清华简《书》类文献横向分系,然后区别不同传本,立体、多层面地考察,才能开辟出先秦《书》类文献研究的新境界。
其四,古文《尚书》真伪问题研究。自南宋至明清时期,吴棫、朱熹、梅鷟、阎若璩、惠栋等人前后相继,从篇目不合、文体伪谬、文辞袭用、职官淆乱、礼制悖谬、地名晚出、历法错乱等诸多层面,多角度、全方位抉发古文《尚书》之罅漏。“祛千古之大疑,立不败之定谳”,“晚书”出自后儒伪造,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。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学者纷纷为之翻案。张富祥、杨善群质疑阎若璩辨伪结论有失公允。郑杰文从墨子引《书》的角度,怀疑梅赜没有造作“晚书”。张岩对“晚书”字频进行电脑检索统计,其结论是作伪难度太高,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。“晚书”真伪公案,再次陷入了长时段、多回合的激烈辩难之中。
《尹诰》为伊尹诰商汤之辞,但古文《尚书》作伪者却理解为伊尹诰太甲。《礼记·缁衣》引《书》“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”和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”,本属于《尹诰》一篇。而辑补者却离析为二篇:一归入《咸有一德》篇;一归入《太甲上》篇。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看,“惟口起羞,惟甲胄起戎,惟衣裳在笥,惟干戈省厥躬”为武丁所言,但古文《尚书》作者却妄改为傅说之辞。先秦时期《书》类文献多线传流,文辞难免增删润色,但时代错位,篇目割裂,言说者张冠李戴,传本的差异、传流的多线难以遮掩“晚书”作伪的痕迹。
其五,汉晋时期古文《尚书》成书过程的再考察。关于古文《尚书》的成书时间,有汉代说、魏晋说、东晋说、刘宋元嘉年间等多种意见。近年来“汉魏孔氏家学”兴起,目的在于从民间传流的视角,证明梅赜本古文的真实、可信。而清华简《书》类文献的面世,证明古文《尚书》当为晚出,汉晋之间的古文传流,就要实现从“证真”向“察伪”的根本性转向。梅赜本古文《尚书》的传授,既然不能与汉儒之本相衔接,那么它是怎么来的?是何时、何人抄撮他书所为?作伪的原因究竟何在?
武丁本是《尚书·说命》的作者,郑玄却错误地理解为“傅说作《说命》”。《礼记·缁衣》引《尹诰》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,自周有终,相亦惟终”,说的是夏桀因暴政虐民,以致上天降丧,邦亡身丧,而郑玄误读为“夏代先哲王以忠信得以善终”。作伪者相信郑玄《礼记注》,对于他的错误说法皆照搬照抄。我们发现,类似的抄袭有四处之多。在作伪者抄撮补苴过程中,郑玄注是不可或缺的参照。郭璞注成书于永嘉四年(310),它两次引用《孔传》,则《孔传》成书必在公元310年之前。古文《尚书》经文的形成要早于《孔传》,则它的成书更在此之前。因此,我们猜测古文《尚书》最终完成时间,很可能在郑玄之后、永嘉四年之前。
其六,对于南宋、元、明、清乃至近现代辨伪成果的重新审视。梁启超盛赞阎若璩为“近三百年来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”,惠栋、段玉裁等人皆服膺阎氏之说,阎若璩成为清代辨伪学的一面旗帜。杨善群、张岩等学者在肯定古文不伪的同时,进而否定阎若璩的辨伪学成就与方法。刘人鹏抨击阎氏的所谓“根柢”,不过是人为预设的假说。赵铭丰认为目前“唯阎是取”的学术倾向,致使毛奇龄《古文尚书冤词》遭受偏颇对待,难以公正地检验毛氏辨伪的内在理路。古文《尚书》公案的定性,与阎若璩、毛奇龄、惠栋等人的辨伪学成就纠结在一起,进而涉及对南宋、元、明、清辨伪方法与范式的重新评价。
天子不能对大臣行稽首礼,阎若璩以此怀疑古文《尚书》作伪,而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记录武丁向傅说行稽首礼,《祭公之顾命》记载周穆王向祭公行稽首礼,两相印证,阎氏的最终结论虽然可信,但论证环节却存在“瑕疵”。站在新材料的基础之上,我们对前贤的辨伪成果及方法,获得了重新审视的必要与可能。
清华简《书》类文献的面世之后,先秦《书》学传流面貌焕然一新,汉晋之际的古文传流需要从“证真”向“察伪”转向,南宋至明清学者的辨伪方法、学术贡献需要重新认定,由此拾级,总结早期古书的生成机制与流衍规律,建构富有中国特色、中国气派的辨伪学理论体系,重写《尚书》学史的曙光已经闪现。
(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” 课题组成员、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;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9日)
